
点击右上角![]() 微信好友
微信好友
 朋友圈
朋友圈

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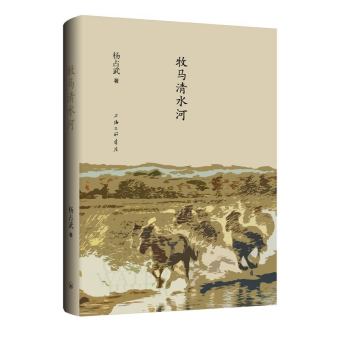
《牧马清水河》,杨占武著,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7月
杨占武先生的散文集《牧马清水河》由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7月出版以来,反响颇好,广获佳评。杨作的特点非常突出,大致有二:一是学理扎实,文笔丰盈,是当之无愧的“学者散文”;二是整部书都围绕着他的故乡宁夏展开,其间浸透着清明的理性和深挚的情感,显示出对家乡的执着。
学者散文在现代中国早已有之,但杨占武的书却别具一格。杨先生是宁夏同心人,专业背景是语言学,有坚实广博的知识储备,同时又历练广泛,也有对文学的不舍眷恋与激情,所有这些都反映在他的作品中。与许多学者散文相似,《牧马清水河》中涉猎的大都是历史话题,不同的是,它讲述的却是一般人比较陌生甚至完全茫然的宁夏历史故事,有强烈的地域性,比如宁夏“河套”何以成为“塞北江南”、历史上宁夏南部清水河流域的“马政”、农牧区域的更替,以及在此繁衍的回、蒙、汉及其他北方民族的历史。更能彰显作品学者气息的是,在切入这些话题的时候,作者使用了丰富的史料,这些材料范围广泛,既有正史,也有大量的古人笔记诗词和地方志,足见作者用力之勤;另外,作者还习惯从语言学和民族学等一般读者不熟悉的角度入手,透露出作者对这些篇章的特殊期待和定位,但他的风格又是放松和随性的,用这种个性化的方式去表达那种“去个性”的学术内涵。
其实,杨占武的可注重处不仅在他的广博和专业,不是他的“掉书袋”,他的“才”和“学”,更在于他的“识”,在于他对历史中那些不被人关注处的兴趣,在于他建立在这些广博知识上的睿智。“牧马”对于宁夏有着极重要的意义,因为“马是古代社会战略性的资源”,而“马又是大型的食草动物,高寒草原是其最佳的栖息地”,正因为此,“雄才大略的汉武帝”才“看中了清水河流域的天然牧场、交通西域等诸多方面的资源价值”,也因为此,“历史上所有的北方民族都几乎入驻过这里。”作品将牧马作为理解古代西北边疆疆土演变的一条线索,不但突出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冲突又融合的关系,也从中获得了一种使文章平添色彩的抒情。实际上,在保证文章有足够学术内涵的前提下,作者始终注意在文字的推进中保持着一种自然节奏,将其中的那份抒情徐徐地抒发出来,成为他散文的一种典型样态。
除了宁夏古代的政治经济之外,杨占武还在书中开辟了更带有他个人特点的领域,即从语言文化和民族关系的角度切入历史,这是他的本业,也更为冷门,但他照样写得饶有趣味。他将当地一些今天仍在使用、却不易理解和归类的词语进行语言和历史辨析,去唤起那些消失在漫漫过往中的民族生命和“遥远的记忆”。当然,这种文化史的方法更专业,学术气息要浓厚得多,对圈内人意味深长,但对局外人却多少有些“隔”。在《大地的记号:驻牧语言图景》《哦,tal,达乐山》《达子住过的地方》等篇章中,我们都会领略到那种人-历史-语言的复杂关系,它们就像作者在《遥远的记忆》里说的:语言“是维系民族情感的纽带,构筑精神家园的基底。”“有了语言对心灵的守护,一个民族的精神便激荡腾跃,生生不息。”
《牧马清水河》使“新时期”的“学者散文”有了一种新的类型。所谓“学者散文”是上世纪80年代文坛上的新现象,更准确地说,是一种新的文学概念。虽然在早期的新文学中,出现了周作人、俞平伯、朱自清以及后来的钱锺书等以学者气著称的散文作家,但那时的作家普遍起点较高,写出的散文自然就有学者气,所以很少有人专门注意到他们的这种“学者”特点,没有一个能够在文学史意义上产生影响的“学者散文”的品类。这种情况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“新时期”文学才有了根本变化,过去那种低调甚至“闲适”的散文又回归了,而很多写这类散文的人都是学者,洪子诚先生因此将这类散文称之为“学者的散文随笔”。但这时候的“学者散文”由于时代的变迁产生了分化。一类是老一代作家,如杨绛、金克木、季羡林、汪曾祺等,他们都是在1949年之前受的教育,笔法带有较为浓郁的民国风味,所写偏重于旧时的人和事,其本身倒未必有多少学术内容。后辈作家呈现的则是不同的风貌。他们成长在高调而抒情的革命文学年代,笔法也经历了深刻变化,代表人物是余秋雨。他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当代散文作家抒情而昂扬的笔调,但却显示出强烈的个人气度和宽阔渊博的学识,被称为“文化散文”。将杨占武和他的《牧马清水河》置于这样的文学史背景下,可以看到他的意义。
杨占武出身乡村,虽然后来成为学者,但早年贫苦乡间生活的经历和浸润其间的共和国文体,使他无法像过去的“学者散文”作家那样,表现出一种冲淡平和的“闲适”风,这是他的散文风格的重要制约因素。就此而言,《牧马清水河》是一部“杂拌”式的散文集,依题材的不同分为四辑。如果说前两辑表现为一种“学者散文”风格的话,后两辑则呈现的是作者作为乡村少年的“前学者”生活录,记录了他在极端贫困状态下的艰难成长:上学时遥远崎岖的山路,需要“寻草”的贫瘠山区,以及饮用水都极匮乏的困窘,当然也有情况改善之后压力的释放。这类散文难以径直称为学者散文,但它的出现也为这种散文增添了一种时代色彩,显示了新的文学时代对这种散文的改造。虽说他写的也是学者散文,但与老一代作家写的那种低调散文差别极大,与余秋雨的所谓“文化散文”也相去甚远。在以往以乡土为背景的作品类型中,知识分子作家与乡村劳动者总是对立——起码是相异——的两类人物,知识分子总是主体,是观察者和写者,而乡村劳动者则是被动的,是被观察和描写的对象,不论作家的目光是鄙视、平视还是仰视。在《牧马清水河》里,这种情况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作品的写作者——学者——正是过去的乡村劳动者,他不但洞悉他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,同时也能体谅他们的情感世界。他们不是他“需要”描写的对象,不需要在观察和描写他们时调整自己的观察和情感尺度——他们就是过去的自己。这种情况当然是现代——尤其是1949年以来——知识分子与农民关系巨大变化的反映,但在“学者散文”这个特殊的品类里,却是一个戏剧性的现象。
(作者:吴进)
